
苏东坡一生爱游名泉,与“泉”结下了不解之缘,并每游必有诗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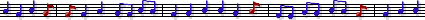
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)十一月,苏东坡39岁,第一次外任密州(今山东诸城市)知府,以清泉自况,就写过《雩泉记》文和卢山《三泉》诗:
皎皎岩下泉,无人还自洁。
不用比三星,清光同一月。
以此显示自己心灵得到净化,思想得到解脱,如同泉寂居深山无人侵犯污染它,始终保持“自洁”纯净的品格。其关键点在于他实现了人与自然(泉)的和谐,人与社会的和谐,人类自身心灵的和谐,形成一种身心皆空、物我相忘的东坡密州超然文化现象。
哲宗元祐七年(1092)二月,苏东坡至扬州,与故友苏伯固游蜀冈。伯固面对美好自然风光即兴赋诗,东坡次其韵抒志言情,送广东提点刑按李孝博奉使岭南:
新苗未没鹤,老叶方翳蝉。
绿渠浸麻水,白板烧松烟。
笑窥有红颊,醉卧皆华颠。
家家机杼鸣,树树梨枣悬。
野无佩犊子,府有骑鹤仙。
观风峤南使,出相山东贤。
渡江吊狠石,过岭酌贪泉。
与君步徙倚,望彼修连娟。
愿及南枝谢,早随北雁翩。
归来春酒熟,共看山樱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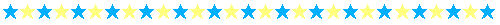

苏伯固:名坚,字伯固,澧州澧阳人,哲宗元祐年间,东坡至杭州时,苏伯固为钱塘寺丞,被聘为“督开西湖”的总指挥,是东坡得力助手。两人友谊深厚,唱和颇多。
李孝博:字叔升,山东人。奉命出使广东提点刑狱(掌刑狱的官)。东坡以泉诗送行,有意识地借泉做廉政的文章。
诗中“渡江吊狠石,过岭酌贪泉”句,讲的是广东南海县石门,有水名贪泉,水澄如镜。相传人饮此水就起贪心,即是“廉士亦贪”。车来马往的过路人,再么唇干舌燥,也只好望泉兴叹,没有一个敢妄自饮用的。然而,以操守清廉著称的、东晋新升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就不信这个邪。他走马上任路过贪泉时,破例酌而饮之,还放歌抒怀:“古人云此水,一歠(chuò淖,‘饮’的意思)怀(招徕)千金;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。”在当初“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,便得三千万”的高额收入形势面前,吴隐之没有把广州刺史当肥缺,始终保持清明廉洁,不占不贪,还贪泉一个清白。任期满了后,他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,与赴任时一样,依然身无长物,两袖清风。吴隐之为官24年,直到去世,仍“淸风肃然,老尔弥笃”,成为一代有名的廉吏。

东坡诗的“酌贪泉”故事启示我们:广州刺史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,如同贪官饮廉泉而不廉一样,可见造物主决定不了泉之贪、廉,更主宰不了官之清、污。是伯夷叔齐也好,还是吴隐之也好,他们不忘先贤廉洁遗训,坚持清廉“不易心”:一颗不变的善良的心、清廉的心、正直的心;即使饮了贪泉也不会改变清廉名节。吴隐之所以有胆识敢饮贪泉,是因为他面对贪泉无贪欲,抗腐拒贪,洁身自好。贪,并非泉的本性,更非人的本性。“不贪为我宝,安步当君车。”(苏东坡《无题》,以下只注篇名)当今社会上流行的“权力腐败论”,我以为不能视为绝对规律,还应以官员个人的本性根基而定。
哲宗绍圣元年(1094)八月,苏东坡59岁,贬官惠州,过虔州(今江西赣州),慕名造访当地名贤隐士阳孝本。他们登郁孤台,游祥符宫,观廉泉,夜话并写诗,言志抒情:
水性故自清,不清或挠之。
君看此廉泉,五色烂麾尼。
廉者为我廉,何以此名为。
有廉则有贪,有慧则有痴。
谁为柳宗元,孰是吴隐之?
渔父足岂洁,许由耳何淄?
纷然立名字,此水了不知。
毁誉有时尽,不知无尽时。
朅来廉泉上,捋须看鬓眉。
好在水中人,到处相娱嬉。
廉泉,在江西赣州报恩光孝寺。宋元嘉中,一声霹雳,泉涌,因施为寺。时郡太守以廉名,因名曰廉泉。([南宋]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)这是本诗中所指的廉泉名。据说我国还有一个名“廉泉”的。安徽合肥包公祠东有一井,水寒而香冽,俗传贪者饮后,头痛如裂,因称此泉为“廉泉”。旁边有祠,亦以包公命名。河中产藕无丝,群众说:“包公无私,竟及于物。”因名此藕曰“包藕”。浙江诗人钱明锵感其事,为题一绝云:“直道清心教化遒,庐阳正气炳千秋。廉泉味冽警顽吏,包藕无私鼠雀羞。”东坡更是有意识地借众多有关泉的古典做廉政的文章。
东坡为何要写《廉泉》诗?“有廉则有贪,有慧则有痴”,“毁誉有时尽,不知无尽时”,“水性故自清,不清或挠之”,上述“廉泉”诗句,揭示了廉与贪、慧与痴、毁与誉等辩证统一的人生哲理;道明了水、人亦即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最真实自然的本质——“清白”。但决定它们的不是物而是人,不是饮什么样的水,而是人临泉有无拒贪(贿)守廉(洁)的自觉意识、清新意识和聪明意识。古人说得好:“不受曰廉,不污曰洁。”[唐]姚合也自警说:“近贫日益廉,近富日益贪。以此当自警,慎勿信邪谗。”只要你具备了“拒贪(贿)守廉(洁)”的这一自觉意识,你就能聪明一生,岿然屹立,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东坡《廉泉》诗里这几个古代名典,无一不在告示我们:人性的塑造是始终离不开“泉”一般的清、明、廉、洁的风范的。“廉者为我廉”,自然会进入“我影投廉泉,水洁清我心”,“好在水中人,到处相娱嬉”的美妙精神境界。

即是晚年,苏东坡仍不忘先贤的鸣泉之风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正月,是时他66岁。北归途中过大庾岭,听幽谷泉鸣,触景生情,联想古琴曲《鸣泉思》,怀念操持正道、不党同的周公一类的君子。回到现实,他已知道哲宗去位犹如“鸣泉故基堙圮殆尽”,焦急不安,徘徊不前,发思古之幽情,作新的《鸣泉思》以寄托晚年之思:
《鸣泉思》,思君子也。君子抱道且殆,而时弗与,民咸思之。鸣泉故基堙圮殆尽,眉山苏轼搔首踟蹰,作《鸣泉思》以思之。
鸣泉鸣泉,经云而潺湲。
拔为毛骨者修竹,蒸为云气者霏烟。
山夔莫能隐其怪,野翟讵敢藏其奸。
茅庐肃肃,昔有人焉。
其高如山,其清如泉。
其心金与玉,其道砥与弦。
执德没世,落月入地。
英名皎然,阳曦丽天。
旧隐寂寂,新篁娟娟。
思彼君子,我心如悬。
谷鸟在上,岩花炫前。
鸣泉鸣泉,能使我菀结而华颠。

东坡笔下的君子周公之风,山高泉清,也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传世作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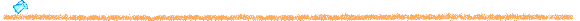
来源:湖北黄州历史文化学会




请输入验证码